论中国佛教的“心”、“性”概念与“心性问题”
发布时间:2023-02-24 15:46:02作者:金刚经原文网
佛教所言的“心性”,简单而言,就是指众生的本性或称之为心的本性。佛学惯常使用的“众生”概念是与其三世六道轮回理论相联系而界定的,实际是指六道轮回之中的一切生命体。佛教将一切生命体称之为“有情”(即有“情识”之意),而将其它存在称之为“无情”(即无“情识”之意)。众生也就是“有情”。这是佛教心性论区别于儒学、道教心性论的基点。由于佛教各宗各派对于“心”及“性”的理解各别,所持的理论立场亦互不相同,因此对心性的阐述就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形态。在此,有必要首先对“心”、“性”两个范畴的含义做些诠释,然后对佛教心性论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做一归纳。
一、佛教中的“心”概念
“心”指众生各各本具之“心”,它在佛学中有种种不同含义,有六识、八识等不同层次的划分,也有从其它角度对其所作的分疏。唐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深有感触地说:“诸经或毁心是贼,制令断除;或赞心是佛,劝令修习。或云善心、恶心、净心、垢心、贪心、瞋心、慈心、悲心;或云托境心生,或云心生于境;或云寂灭为心,乃至种种相违。”[①]在宗密看来,诸经诸论所说千差万别,然而看似杂乱无章,实际却有大致的层次与类别。概括起来,宗密这样说:
泛言心者,略有四种,梵语各别,翻译亦殊。一、纥利陀耶,此云肉团心。此是身中五藏心也。二、缘虑心,此是八识,俱能缘虑自分境故。此八各有心所、善恶之殊。诸经之中,目睹心所,总名心也,谓善心、恶心等。三、质多耶,此云集起心,唯第八识,积集种子生起现行故。四、乾栗陀耶,此云坚实心,亦云贞实心。此是真心也。[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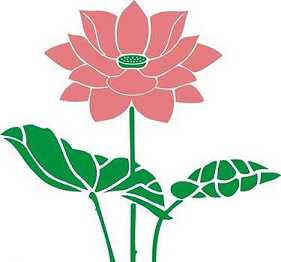
这里,“肉团心”多指众生身体内的肉体之心即心脏,古人误将其当作意识产生的根源。此义,早期佛教经典多有涉及,但后来仅有密教有所强调,其它大乘佛教诸宗诸派均不大论列。中国禅宗语录偶有使用,然而意义已有所变化,多指众生起用动念的“当下”之心。“缘虑心”指心的认知功能,唯识学以之泛指八识,其它宗派则仅以之指称六识。“肉团心”、“缘虑心”有认识主体的含义,可以归并为主体之心。“真心”指心所具有的常恒不变的清净性质,可以将其看作众生的形而上本体。这样,“心”的含义就可以简明地归纳为两种:一是作为主体的“心”,二是作为本体的“心”。前者可称之为心用,后者可称之为心体。“集起心”为唯识学所特别强调,特指第八阿赖耶识。由于慈恩宗并不认为“心”有不变的部分,其所言的阿赖耶识本身就具有心体的含义,心用则以前七识充当。
二、佛教中的“性”与“心性”概念
“性”的含义也颇为复杂,在佛教经论之中有着广泛的运用。尽管佛学以理论思辨和名相的严整著称,但对“性”这一概念的使用仍然显得异常混杂。佛学对于“性”的最一般性解释,就是“法”的自相,也就是佛学之中常说的“自性”。如《瑜伽师地论》所云:“云何‘性’?谓诸法体相。若自相,若共相,若假立相,若因相,若果相等。”[③]此中所举都属于“法”的可变的性质。而佛学中又有“法性”一语,此语之意为“诸法实相”,也就是诸法的最本质属性即“空性”。在此所言的“性”的两种含义,前者与“心”相联系构成“心相”或“心用”;后者在中国佛教心性论中略同于“理体”。除此之外,法相唯识宗通常还在两个层面上使用“性”的概念:一是“识性”,二是“实性”。“识性”指八识各别的“自性”或性质,“实性”指“圆成实性”,也就是真如理体。
中国佛学有“性宗”和“相宗”的区分。这一区分也贯穿在对“性”这一名相的不同理解上。智顗在《摩诃止观》卷五中释之为:“性以括内,总有三义:一不改名性。《无行经》称‘不动性’,‘性’即不改义。又性名性分,种类之义,分分不同,各各不可改。又性是实性,实性即理性,极实无过,即佛性异名耳。”[④]智顗所说“性分”之“性”指“自性”,即诸法以及众生各别的特殊规定性。用于前者不属心性论概念,用于后者则指众生的“体性”,亦即根机。如此,智顗所说心性论之“性”就含有“不改”、“理性”及“体性”三义。“理性”即实相、佛性、真如、法性,而受中观学影响甚深的“性宗”所认可的究极意义上的“不改”者,唯有佛性、真如。因此,上述三义实际上可归并为二义:不改之性即真如理体与众生的体性。在心性论意义上,法相唯识宗所言的“识性”、“种性”、“唯识实性”和“实性”属于不同的层面。“识性”从“心识”层面对众生的根性或本性的界定,而最根本的“识性”则是藏识;“种性”又称“种姓”,即众生所具解脱成佛的“根机”或根据;“唯识实性”或简称“实性”是指“圆成实性”即真如理体。在唯识宗中,“识性”是可以改变即“转依”的,而“实性”则作为“最高真理”是不可改变的。但从哲学本体论的视域观之,“藏识之性”才是“本体”,而“唯识实性”仅仅是“理体”。显然此宗所言的“理体”与心体是两分的。
如果综合以上所言,中国佛教心性论所言之“性”即可简要归结为二义:一为本体之性,在“性宗”指“理性”,在“相宗”指“识性”。二为根性、体性之性,在“相宗”指种姓、种性,在“性宗”则指根机。为了更清晰地显现“心”、“性”两个范畴的含义,特别是二者之间的联系,可以将上述疏解简化为如下图示:
主体之心
肉团心
缘虑心
体性
识性
体性之性
本体之心
真心
集起心
理性
藏识
本体之性
性宗
相宗
性宗
相宗
心
性
以上,为论述的便利而勉强对“心”、“性”二范畴作了简单界定和图示。在疏解过程中,我们说“性宗”的“理性”义其实就是指实相、佛性、真如、法性,而“真心”概念又与“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密切相关。因此,佛教心性论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重要范畴“理”。大乘佛教是以解脱成佛为终极目标的,因而佛性、佛之体性是其宗教解脱论的必然环节。大乘佛教中的“佛”实际上是一抽象理体,真如、实相、佛性、法界、法性、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如此等等,均是佛之体性的异名。尽管这一“理体”在不同宗派中的地位不同,与主体之心的结合方式也各不相同,但所谓成佛就是修现或悟见这一“理体”的规定是相同的。大乘佛教对于“如来”的典型解释“乘如实道,来成正觉,来化群生”,突出了佛的“觉他”功德,但佛之体性却是“真如理体”。不过,对于“佛性”范畴,“性宗”与“相宗”的诠释各不相同。印度护法系唯识学以“无漏种子”解释佛性,而中国的法相唯识宗则以“理佛性”和“行佛性”诠释佛性,所谓“理佛性”即真如理体。这一解释与“性宗”有些相近。中国化佛教诸宗——天台、华严和禅宗是以“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解释佛性的,与此相近的概念还有真如、实相、中道理体等等。这是受印度如来藏系经典,特别是南北朝传入中土的古唯识学的影响的结果。隋代净影慧远这样解释佛性:
一者种子因本之义。所言种者,众生自实如来藏性,出生大觉与佛为本,称之为种。种犹因也。
二、体义名性。说体有四:一、佛因自体,名为佛性,谓真识心。二、佛果自体,名为佛性,所谓法身。第三、通就佛因佛果同一觉性,名为佛性。其犹世间麦因麦果同一麦性。如是一切当知,是性不异因果,因果恒别,性体不殊。此前三义,是能知性,局就众生,不通非情。第四、通说,诸法自体,故名为性。此性唯是诸佛所穷,就佛以明诸法体性,是云佛性。此后一义,是所知性,通其内外。
三、不改名性。不改有四:一、因体不改,说之为性,非谓是因常不为果说为不变,此就因时,不可随缘。……因体即是如来藏性显为法身,体无变易,非如有为得果因谢,就体以论,故名不改。二、果体不改,说名为性,一得常然,不可坏故。第三、通就因果自体不改名性……佛因佛果,性不改故,众生究竟必当为佛。……第四、通说诸法体实不变名性,虽复缘别内外染净,性实平等湛然一味故曰不变。此是第三不改名性。
四、性别名性。性别有四:一、明因性别异于果。二、明果性别异于因。第三、通就因果体性别异非情故。四、就一切诸法理实别于情相虚妄之法,名之为性。[⑤]
净影慧远的解释代表了后来中国佛教“性宗”对佛性的一般理解,因此不嫌文长而引之。其要点如下:第一,佛性是众生成佛的根据即“因”;第二,佛性是佛与众生共同的“体性”——真识心、佛果法身、觉性;第三,不改之性,此是就佛因与佛果之间的关系角度诠释“理体”的不变不改的性质;第四,作为成佛之因的佛性与佛之果位又是不同的,而一切诸法之中所蕴涵的与虚妄之法不同的“理”就是“性”,简称为“理性”。在此,应该特别指出,慧远所说的“不改不变”被现代学者当作“真常”理解。实际上,慧远说的很明确,所谓“不改之性”有四方面:其一是显为法身的如来藏因体不改,其二是证得的佛果不再改变,其三是作为佛因、佛果的自体是不改的,其四是诸法所具的本质——空性是不改不变的。这四方面并不是如日本学者所言的不改不变的“基体”之义,而是从众生成佛的根据以及诸法的本质即“空性”而言的。前者说的是众生成佛的“绝对”可能性,后者说的是世间诸法所具的终极“真理”——诸法实相。从众生成佛的角度而言,众生之心所蕴涵的绝对不变的清净性是其之所以能够解脱的终极根据,而此“不改不变”是从佛因、佛果的一致性着眼的,并非是说有一个不变的所谓“真心”作为众生和佛之间共同的“所依”。净影慧远的这一对“性”的理解以及其诠释之中所体现的将佛性与众生之心相结合的向度,对中国佛教心性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⑥]
与将“心”与“性”分开使用不同,佛教典籍中时常将“心性”连起来使用。从今日的学术立场言之,“心性”应该是梵文citta_prakrti的意译。但若想在早期汉译经典之中做追根求源式的研究是有相当难度的。因为据现存梵文原本,我们已经很难搞清楚佛典中所有的“心性”一词是否均为citta_prakrti的对译,而古代汉语以单音字为主的特点更是我们难于分清楚到底是一个范畴还是两个词。即便是心性论发达之后的佛教思想家,也很难说其著述中对“心性”一语的使用是完全一致。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们只能说,汉译佛典中早就有了“心性”一语,至于是否为一独立的哲学范畴尚难一概而论。[⑦]罗什所译《成实论》在记述部派佛教心性思想时多次用了“心性”一语。此后,北凉昙无谶的译籍也数次出现“心性”一语,如在其所所译的《大方等大集经》中有多处用例:
一切众生心性本净。性本净者,烦恼诸结不能染著,犹如虚空不可玷污。心性、空性等无有二,众生不知心性净故,为欲烦恼之所系缚。如来于此而起大悲,演说诸法,欲令知故。[⑧]
一切众生心本性,清净无秽如虚空。凡夫不知心性故,说客烦恼之所染。若诸烦恼能污心,终不可净如垢秽。诸客烦恼烦恼障覆故,说言凡夫心不净。如其心性本净者,一切众生应解脱;以客尘烦恼障覆故,是故不得于解脱。[⑨]
《大般涅槃经》说:“心性异故,名为无常。所谓声闻心性异,缘觉心性异,诸佛心性异。┅┅善男子,以是义故,当知心性各各别故,当知无常。”[⑩]不过,应该特别注意,“心”、“性”连用的语意非常复杂,在不同语境之中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意义,需要在文本分析中仔细辨析才行。如上引《大集经》中数例“心性”即为众生之心的本来状况,而上引《大般涅槃经》卷十四所言的“心性”显然不能作本性或本来状况理解,只能理解为“心”的性质即“体性”。
中国佛学各个宗派,甚至于不同的佛学家对于“心”与“性”的理解和诠释都有或细微或显著的差别,而各家各宗心性论的成就首先就体现在各自对“心”、“性”和“心性”范畴的独特诠释上。正因为如此,本文对“心性”一语采取最宽泛的界定,即“心之性质或本性”。在这一宽泛定义之下,我们才可以较为方便地对各个历史时期以及各宗各派的心性思想作些归纳和比较研究。不过,为便于读者把握古代思想家的大致思路,我们仍然以“性宗”和“相宗”的传统分类对心性论的范畴系统作大致的说明。
在佛教看来,在六道轮回之中沉沦的众生,唯一的希望和要求应该是成就佛果。因此,佛学的首要目标就应该是为众生寻找成佛的根据,而此根据必然要落实于众生之心体中方才符合佛教的解脱论原则。这样,围绕着心、佛、众生三者,以心体与理体的关系为核心,佛教的心性论体系便由此展开。在中国佛教心性论中,以中观学之实相与如来藏系的真如来诠释理体是各家各宗的通义,分歧不大。而中国佛教心性论之所以丰富而略显繁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诸家诸宗依据不同的经典,对于“心”及“性”赋予各不相同的意义,并且在此基础上建构起各具特色的心性论体系。
三、佛教的“心性论”问题
对心性问题的讨论,早在部派佛教就开始了。其互相对立的两个命题──心性本净与心性本不净,成为大乘佛教心性论的基础性范式。如来藏系经典承续的是前者,唯识学承续的是后者。中国佛教心性论是印度佛教的“继续”,也是印度佛教的发展。从“继续”而论,部派佛学的“心性本净”思想以及与此相关的如来藏学说,“心性本不净”思想以及与此相关的唯识学,均相继传入中土。[11]从“发展”而论,中国佛教心性论也不是完全照搬印度佛学的现成思想,而是有许多变化,有许多创新。这些,不仅可以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涅槃学派、地论学派及摄论学派对心性问题的讨论之中看出,而且突出表现于隋唐时期天台、华严、禅宗等所谓中国化佛教宗派之中。然而,即便是被认为最接近印度瑜伽行派原貌的法相唯识宗,其心性论思想也有自己独特的方面,并非完全等同于印度佛学。这一方面与中国独具的文化传统及心性论特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佛学大师们以“四依菩萨”精神从事的创造性诠释密切相关。与印度佛教相比,中国佛教更为重视心性问题。南北朝时期虽曾热烈地讨论过心性问题,但由于条件的限制,并未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不过,这一时期所形成的心性论资源,为隋唐佛教诸宗的综合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殆至隋唐,中国佛教便形成了四种既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又各具特色的心性论范式。这些范式,不仅对后来的中国佛学以及儒学、道教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东亚其它国家的佛教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综观隋唐佛教心性论,其理论体系由以下四个环节构成:其一为“心体与理体”。中国佛教心性论的首要目标是为众生成佛寻找形而上的根据,而为了将此根据落实于众生之心中,对众生本性的判定便是当然的理论前提。中国佛教心性论的根基便是如何论定众生之心体与真如理体的关系。在印度佛学相关命题的基础上,中国佛学引入了“觉”与“不觉”、真心与妄心、善与恶等理论范畴以分析众生之心的染净以及与理体的关系。其二为“生佛与佛性”。大乘佛教中,众生与佛的关系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而将“生、佛”关系与众生的心性联系起来,正是大乘佛学的特质所在。换言之,将“心体与理体”的关系问题贯注于“生、佛”关系之中,正好是所谓“心、佛、众生”“三法”之所指。其三为“唯心与唯识”。在上述问题的探讨之中,由于理论本身的逻辑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宗教解脱的需要,中国古代佛学家又将其理论触觉扩展到对“色、心关系”的讨论。这样,本体与现象的关系问题便成为佛教心性论的重要内容。不过,应该指出,佛学并不是从一般意义上去谈论心物关系。“色、心关系”又称“心、法关系”,而佛学中的“色”与“法”并不能简单地将其与普通所说“物”或“物质”等同起来。“色”与“法”实际上是指主观意识之对象化所形成的“意义”及其“世界”。佛学之所以热衷于谈论心物关系,其深层用意在于为众生解脱成佛提供心性论依据。所谓解脱,从“心”与“法”的关系而言,其实就是斩断心与物及其“意义世界”的关联。其四为“心性与解脱”,即“心性”的证得或“转变”。佛教心性论的所有理论,其归趣均指向修行解脱论。这是佛学的宗教特质使然。而中国佛教心性论的完整性和严密性正好就体现在这里。理论色彩浓厚的天台、华严、唯识、禅宗,由各自特有的心性论立场所决定,各各倡导独具自宗特色的修行解脱论。换言之,隋唐佛教诸宗无不将自家的心性论宗旨贯注于其所倡的修行解脱论之中。概括而言,隋唐佛教诸宗,特别是理论色彩浓厚的天台、法相唯识、华严、禅宗,由于对于“心”、“性”二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释义各异,因而对于生佛关系及其佛性如何落实于众生的心体之中等等重大问题的回答亦各不相同,并由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四种心性论范式。
中国佛教心性论,既是本体论,也是修行解脱论。作为本体论,它既在心、佛、众生“三法”的框架之中探讨心体与理体、心性与佛性的关系,也在更大范围内追究诸法之所以存在的根据,进而现证诸法的真实相状。作为修行解脱论,它以解脱成佛为终极目标。由于众生本具真如佛性,众生心性本净本觉,因而现证心性、返观心源即可成佛。这是台、贤、禅等“性宗”在心体、理体合一基础上所形成的修行法门。由于倡心体与理体两分,唯识宗则以“转依”即转变心体而以真如为“依”的“转识成智”为修行成佛的门径。它并不限于身心的转易,而且还联系着事相的变革,在认识和行为的交互作用,亦即主、客两方面的交互变化之中实现认识的彻底的如“理”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佛教心性论也是一种特殊的人性论。尽管佛教惯于以六道轮回中的所有生命体为对象讨论心性问题,但“人”无疑是其理论最深切的关注点,因而其心性论之中本来就含有明显的人性论倾向。中国佛学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倾向,宋代以后,其人性化、伦理化的特质终于由潜流变成主流。中国佛教心性论打通了本体论、修行解脱论与人性论的隔膜,将三者较为完满地结合为一体。而这一特质的形成既与儒学、道家及道教的渗透有关,也是佛学对儒学、道教的最大影响之所在,更是佛学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
中国哲学一向被称为心性之学。其实,重视“心性”,将心性论提升为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从隋唐佛学开始的。印度佛学尽管从部派佛教始,就讨论心性“本净”还是“本不净”的问题,大乘佛学的如来藏系经典和唯识学系对其也做过深入的讨论。但是,如来藏系经典在印度并未如中观、唯识系一样发展为相应的学派。在中国,情况则完全不同。随着《大涅槃经》的传译以及竺道生等佛学大师的弘扬,心性问题随即成为中国佛学的中心论题。随后,围绕菩提流支、真谛译籍所形成的“地论学派”和“摄论学派”以唯识学理论将心性问题的讨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而流行于此时的《大乘起信论》更是集中阐明了心性论思想。可以这样说,尽管心性问题并不是南北朝佛学的唯一热点,但是,这一问题无疑是当时最有理论深度的佛学课题。作为中国佛学巅峰的隋唐佛教诸宗,特别是天台、法相唯识、华严宗和禅宗,心性思想成为其立宗的根基所在。上述四宗各自建构的相当完备且独具特色的心性论体系,标志着中国佛学心性思想的最终成熟。
如此完备、成熟的心性思想,一方面,不能不对鼎足而三的另外二教──儒教和道教,构成强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佛教心性论实际上也成为儒、道二教建构自己理论体系的有益的思想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没有成熟的佛教心性论,儒学、道教即便可以独立建构出自己的心性论体系,也不会是我们今日所看到的模式。不过,也应该看到,虽然佛学是由印度移植而来的,但中国佛教心性论又是紧紧扎根于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之中的。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学、道家和道教思想在许多方面又不能不影响到佛教心性论的发展路向。在印度佛学之中,影响并不显赫的如来藏思想之所以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正是中国僧俗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而自主选择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佛教心性论又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不过,在目前情势下,需要注意的倒不是对佛教中国化程度的抑评,反而是那种过度的“抬高”,更容易导致对中国佛教应有成就和贡献的解构。支那内学院的“反传统”主张与日本“批判佛教”就是如此。
中国佛教心性论的主体部分是由如来藏思想及其“性觉”说而来,但是近代佛学界对其却难以取得共识。近代中国有以支那内学院为中心的反传统派[12]和以武昌佛学院为核心的维护传统派,日本学界也一直有一批学者对《大乘起信论》等“疑伪经”持一定程度的怀疑态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日本有学者撰文宣称“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本觉思想不是佛教”,认为以此为基础的汉化佛教思想是“伪佛教”。这一思潮被概括为“批判佛教”。“批判佛教”所提出的问题又波及欧美佛学界,得到了广泛讨论。从整体而言,持“批判”立场的学者只是少数,但其倡导的观念对中国佛教及其受中国佛教影响而形成的东亚传统佛教却具有较大的颠覆性。因此,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批判佛教”所涉及的问题很多,而支撑上述两个命题的核心理据是“基体”说,认为作为“基体”的如来藏和性觉之心体与佛教的“无我”观、缘起论是相互矛盾的。本研究尽管并非直接针对“批判佛教”,但希望能够有助于回答这一挑战。如此观之,对中国佛教心性论的分析评估实际上便牵扯到如何看待佛教中国化的成败得失,以及如何界定中国僧俗对世界佛学的贡献等等重大问题。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研究,不仅对更好地估价佛教中国化的历程,而且对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儒、道、释三教的互融互渗关系,丰富我们对于中国哲学的认识,都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尽管近年来佛教心性论是一个热门话题,但相当一部分论著仅仅从佛性的角度谈论心性,甚至有将心性论与佛性论等同的趋向。在我们看来,尽管作为众生成佛终极依据的佛性与众生之心性有着紧密的关系,但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佛教心性问题涉及的领域更为宽泛,也更带有哲学本体论的致思倾向[13]。实际上,佛教心性论既是以宗教解脱为旨归的“心体论”与修行论,也是以“心体”与诸法的关系为玄思对象的哲学本体论。因此,有必要在这一较新的基点上,对佛教心性论做些研究。
(原刊于《宗教学研究》,2002年第1期。)
--------------------------------------------------------------------------------
[①] 《禅源诸诠集都序》卷1,《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2卷第2册,第428页。
[②] 《禅源诸诠集都序》卷1,《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2卷第2册,第429页。
[③] 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13,《大正藏》第30卷,第345页下。
[④] 隋智顗《摩诃止观》卷5,《大正藏》第46卷,第53页上。
[⑤] 隋慧远《大乘大义章》卷1,《大正藏》第44卷,第471页。
[⑥] 与庐山慧远将“法性”当作“真神”来诠释“至极以不变为体”,净影慧远的解释并无将“真识心”“实体化”的倾向。这是中国佛教心性论自觉地消解在心性本体问题上的“实体化”向度的成功一例。净影慧远的这一努力在隋唐佛教诸宗心性论之中得到鲜明的反响。
[⑦]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主张对于中国佛教心性论最好是以“问题”贯穿其间进行研究。若拘泥于文献的本来用语,则很难有确切的结论。本著就是采取这一作法而将佛教心性论分为四大层面的“问题”进行研究的。佛教各宗各派心性思想异常复杂,为了便于把握,本文在吸收古代佛教文献相关说法的基础上,以“理体”指解脱成佛之后所证得的“最高真理”,也是是佛教所说的“真如”、“实相”、“法性”等等,“心体”则指众生之心的“本来”状况。佛教心性论的主要理论“问题”则见下文。
[⑧] 北凉昙无谶译《大方等大集经》卷2,《大正藏》第13卷,第11页下。
[⑨] 北凉昙无谶译《大方等大集经》卷13,《大正藏》第13卷,第90页中。
[⑩] 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14,《大正藏》第12卷,第446页上。
[11] 部派佛教对于“心性本净本不净”的讨论在安世高和竺法护的译籍中已经有所反映。安世高在《〈安般守意经〉序》中以镜明来比喻禅修而成的境界,似乎持的是心性本净的立场。而竺法护所译《度世品经》卷5以及《大宝集经》卷8〈密迹金刚力士经〉、〈大方等顶王经〉就有“心本清净”等等义理。
[12] 台湾学者蓝吉富称其为“反传统倾向”,本文采用其说。详见《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2期所载《现代中国佛教的反传统倾向》一文。
[13] 港台学者马定波在其所著《中国佛教心性说之研究》(台湾中正书局,1980年第2版。)一书中,从“心性现证”的角度对中国佛教心性论进行了系统研究,其论甚为精审,唯其所论仅仅限于“心性解脱”之一隅,有忽略佛教心性论本来就具有的更为广阔的理论意义之虞。而港台新儒家阵营,如牟宗三、唐君毅、方东美等等,对于佛教心性论的研究分析,更多地是从儒学与佛学思想之比较的角度出发的,而且其所具有的建构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的理论意图更限制了其研究应该具有的“价值中立”的“客观”立场。倒是近代以来,欧、美、日以及港台、大陆佛学界对于“如来藏”思想的研究,虽未冠以“心性论”之名,但是,不可否认其涉及的领域就是佛教心性论的固有视域。不过,欧、美、日的学者更多的将其研究中心放在了“如来藏系经典”的上,而对中国佛教在此基础上的新进展却缺乏足够的重视。中国大陆学界以赖永海先生的《中国佛性论》为开端和理论代表,对于佛性思想的研究很有深度,完全可以作为佛教心性论研究的理论基础。笔者在博士论文《中国佛教心性论研究》,就是在中国佛性思想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方面试图拓展佛教心性论的研究视域,另一方面又试图在以修行解脱为特质和终极价值的佛教心性论与作为“哲学本体论”的佛教心性论之间,寻找其共通性与理论连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