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兴与佛教
发布时间:2023-02-13 15:53:17作者:金刚经原文网姚兴与佛教
陈坚
“长安佛教”的特色之一就是“帝王佛教”,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后,历朝历代以长安为都的帝王都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我这里想说说十六国时期后秦皇帝姚兴(355—416)的佛缘,说说姚兴与佛教有关的那点事。如果有两个机会同时放在我面前,一是去纽约看姚明打球,一是去长安听姚兴谈佛,那我宁愿选择长安,选择姚兴。
姚兴的性格中有某种文人的气质,“姚兴虽为羌人之后,但从小受到比较好的文化教育,虽处变乱中,学习不辍,不以兵难废业”1,在他还是皇太子的时候,即使戎马倥偬,也要忙里偷闲与“舍人梁喜、洗马范勖等讲论经籍”2,姚兴的这种文人气质实际上就是其日后能得以全身心地接受佛教的良好根机,而且这也保证了姚兴在当了皇帝之后不会以佛教徒的偏狭心态而是以文人的广博胸怀来对待佛教,即没有独尊佛教而将佛教定为国教,“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姚兴绝对不是一位‘佞佛’的君主。他的眼界比较开阔,对儒学也很重视”3,如“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儒硕德,经明行修,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兴每于听政之暇,引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凉州胡辩,苻坚之末,东徙洛阳,讲授弟子千有余人,关中后进多赴之请业。兴赦关尉曰:‘诸生谘访道艺,修已厉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于是学者咸劝,儒风盛焉。”4在当时一般的国民还受制于严格的人口管理而难有随意走动的自由身的情况下,姚兴对儒生网开一面,允许他们免签证出入关卡,在后秦自由往来进行学术交流,有如此宽松的知识分子政策,儒风焉能不盛?后来,这种宽松的知识分子政策又被姚兴如法炮制地延用于佛教沙门,随即又造成了佛教在后秦的繁荣。
姚兴的文人气质以及后秦的浩荡儒风使得当时的“长安佛教”与其说是宗教形态的还不如说是文化形态的,长安的这种文化形态的佛教在鸠摩罗什(344—413)来到长安后更是进一步达于极盛,因为“鸠摩罗什在长安,社会一流的人全都聚集长安”。5
鸠摩罗什是西域龟兹着名的佛教学者,在那个战事频仍的年代,他的命运也颇富戏剧性。382年,前秦苻坚派将军吕光攻陷龟兹,俘获了鸠摩罗什,在归途中,吕光获悉苻坚为东晋所败,便占据凉州,自立后凉国为王,鸠摩罗什于是也就以俘虏的身份羁留凉州达16年之久,其间由于吕光对佛教不甚感兴趣,他这样的佛教人才居然只是被委以军政咨询之闲职而基本上无涉于佛教,直到“401年,后秦姚兴出兵西伐吕凉,凉军大败,鸠摩罗什被邀进长安,受到国师般的礼遇。姚兴是北方诸国中最有作为的帝王之一。他注意招人才,提倡儒学与佛学,一时长安集中了许多学者,成了北方文化重镇,影响及于江南和西域、天竺。他请罗什入住逍遥园西明阁,组织了庞大的译经集团和讲经活动”6,并且经常亲至逍遥园参与其事,“兴如逍遥园,引诸沙门于澄玄堂听鸠摩罗什演说佛经。罗什通辩夏言,寻览旧经,多有乖谬,不与胡本相应,兴与罗什及沙门僧略、僧迁、道树、僧叡、道坦、僧肇、昙顺等八百人,更出大品,罗什持胡本,兴执旧经,以相考校,其新文异旧者会于理义。续出诸经并诸论三百余卷。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仕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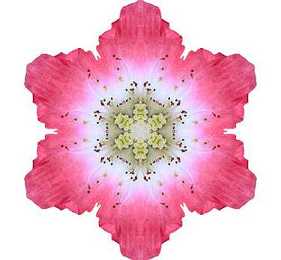
吕光把鸠摩罗什“俘”到凉州,作为俘虏的鸠摩罗什一时“英雄无用武之地”,其卓越的佛教才华难见天日,他的落魄失意是可想而知的,幸亏不久来了个救星姚兴,将他“邀”进长安,为他建立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国家佛经译场兼国家佛教讲堂,“在姚兴的支持下,鸠摩罗什译出经、论三百余卷”8,这才成就了后来彪炳千古的作为中国佛教史上“四大译经家“之首的鸠摩罗什——一“俘”一“邀”之间,鸠摩罗什便从地狱升到了天堂!如果没有姚兴,鸠摩罗什恐怕只能默默无闻地老死凉州了。然而,当我们当代人在津津有味地阅读署名“鸠摩罗什译”的《金刚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等着名汉译佛经时,又有多少人会想到姚兴呢?许多人可能连姚兴是谁都还不知道呢?毕竟姚兴不是象李世民、朱元璋那样的大皇帝,其国既小,国祚又短,一隅之国而已,可以说,姚兴乃政治上的侏儒、佛教上的巨人。南朝的梁武帝(464—549)也差不多是这样的皇帝,只是与姚兴相比,“四次舍身同泰寺”的梁武帝颇有点“佞佛”的味道。
鸠摩罗什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的大乘佛教空宗思想家。在鸠摩罗什来到长安之前,一般的中国人甚至佛教徒,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大都视佛教为神仙方术,对佛教的真意义并不了解,是鸠摩罗什在姚兴支持下的大规模的译经和讲学活动使得印度佛教大乘空宗的思想渐渐在中国落地生根。在知识界,鸠摩罗什的高足僧肇对大乘空宗思想有最为系统的把握,他那由四篇论文构成的《肇论》就是明证;而在政界,姚兴堪称是其中学得最好的,因为他经常光顾逍遥园,有机会受鸠摩罗什耳提面命,焉能不“近水楼台先得月”?从姚兴留下来的少量佛学言论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大乘佛教空宗思想的准确理解,如他在谈到“般若”时说:
众生之所以不阶道者,有着故也,是以圣人之教,恒以去着为事,故言以不住般若。虽复大圣玄鉴,应照无际,亦不可着,着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遣所寄,泛若不系之舟,无所倚薄,则当于理矣。9
姚兴将“般若”称为“不住般若”,所谓“不住”即是不执着。在姚兴看来,既不着有,又不着空,“若不系之舟,无所倚薄,”这就是“般若”的含义。姚兴对“般若”的这种理解显然是十分到位的。姚兴由于对佛学有精到的理解,所以也经常受邀(也许是毛遂自荐、自告奋勇)参与鸠摩罗什的译经活动,并且他身边的那些官僚大臣也都喜欢向他讨教佛学问题(安成侯姚嵩甚至还就“佛义”正式表奏姚兴10),他则来者不拒,乐于耐心地帮他们答疑解惑,俨然以佛学专家自居。不过,从整个中国佛教史上看,姚兴真还有居功自傲的资本,因为,如果说中国佛教思想的主流是大乘空宗(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除唯识宗以外的七大宗派都属于大乘空宗),那么这个主流的源头就是从西域来到长安的鸠摩罗什,而鸠摩罗什又是姚兴请来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姚兴才开启了中国佛教大乘空宗这一主流。
姚兴不但在佛学理论上颇有造诣,而且由于对佛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信佛而不佞佛,所以在生活中也是一位标准的正信佛教徒,他曾“下书禁百姓造锦繍及淫祀”11,也就是不许百姓举锦繍、抬猪羊到庙里求神拜佛搞迷信活动,同时他还因为信仰佛教的缘故,经常举行大赦,以显示其慈悲之佛心,而最能说明其慈悲之佛心的还是下面这件事:“兴从朝门游于文武苑,乃昏而还,将自平朔门入。前驱既至,城门校尉王满聪被甲持杖,闭门距之,曰:‘今已昏暗,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门不可开。’兴乃回从朝门而入。旦而召满聪,进位二等。”12姚兴出门游玩,回来晚了,守门人王满聪因天昏暗看不清他的真实面貌而拦着不让进,姚兴也随缘不生气,改从另门而入,并且第二天还因为王满聪的负责任表现而提拔了他。



